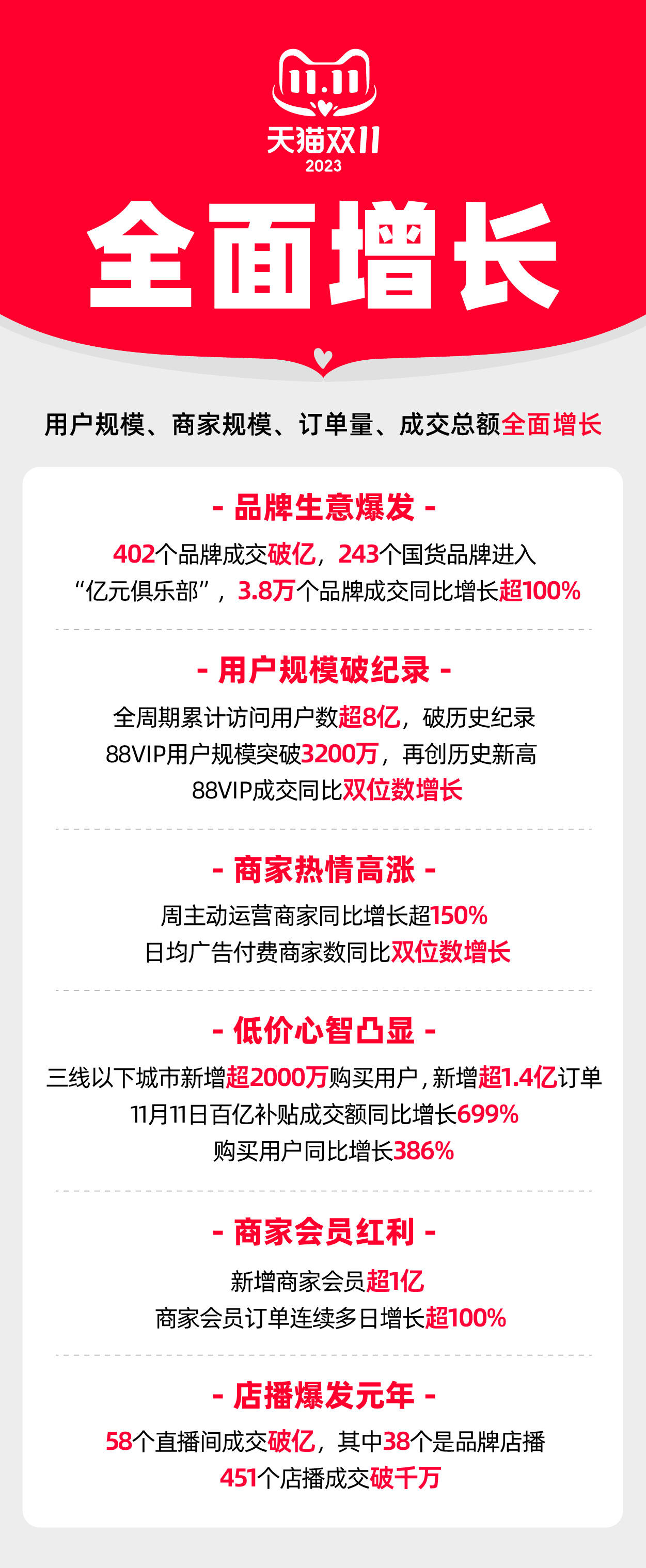都市青年的社交孤獨(dú):網(wǎng)絡(luò)替代線下 遠(yuǎn)離原有社交圈
來源:工人日報(bào)
2018-12-09 07:48:12
都市青年的社交孤獨(dú)
晚上7點(diǎn)下班后,坐了一個(gè)半小時(shí)的地鐵,又走了20分鐘的路,在北京一家外貿(mào)合資公司工作的陳曉睿,終于在9點(diǎn)前到達(dá)約定地點(diǎn)和閨蜜見面,半年多沒見的兩人只聊了一個(gè)小時(shí)就各自又鉆進(jìn)地鐵。陳曉睿10點(diǎn)半走出地鐵后,在寒風(fēng)中走了很久才到家。“到家看表,將近11點(diǎn)。”
在此之前,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個(gè)城市的兩個(gè)人,已經(jīng)半年多沒有見面了。來回路上將近4個(gè)小時(shí),見面只有1個(gè)小時(shí),陳曉睿突然明白了微信朋友圈里流行的那句話,“如果不是‘生死之交’,不會有人和你在工作日的晚上,吃一頓不談利益的飯。”
頻繁且不固定的加班,長時(shí)間的擁擠通勤,加上網(wǎng)上交易取代線下社交,許多都市青年,感受到了社交孤獨(dú)。
加班與通勤占用時(shí)間精力
“有時(shí)候,一整天,我沒和同事之外的人說上一句話。”在北京中關(guān)村一家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工作的馮悅,一直想和中學(xué)同學(xué)聚會,但每次討論聚會的結(jié)果,就是大家七嘴八舌在微信群里討論一番,但是誰都抽不出時(shí)間,無疾而終。漸漸地,聚會這件事情,也就無人提起了。
馮悅算了一筆賬,“就算按正常時(shí)間晚上6點(diǎn)半下班,各自到達(dá)中間地點(diǎn),怎么也得7點(diǎn)半到8點(diǎn)之間,晚高峰的地鐵很擠,公交時(shí)間不靠譜。到了集合地點(diǎn),飯店排號,排個(gè)半個(gè)小時(shí),趕在8點(diǎn)半前吃上飯,聊1個(gè)小時(shí)就得各自回家,商場10點(diǎn)就關(guān)門,商家9點(diǎn)半就開始結(jié)賬清人。就算這樣,到家也要11點(diǎn)左右,第二天還得6點(diǎn)早起上班。”
能見面一個(gè)小時(shí)的前提,是不加班。無憂精英網(wǎng)進(jìn)行過一次13682人參加的調(diào)研,結(jié)果高達(dá)93.32%的受訪者,工作需要加班。
漫長的通勤距離,也讓都市青年不得不放棄社交聚會。根據(jù)前程無憂發(fā)布的《2018職場人通勤調(diào)查》,北京上班族的平均通勤半徑是16.79公里,在上海,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上班族通勤半徑超過25公里。在通勤時(shí)間上,上海上班族單程通勤59.56分鐘,另外,在一線城市,還有相當(dāng)一部分上班族是跨省上班,比如從燕郊到北京、昆山到上海等。
即便到了周末,留給社交生活的時(shí)間依然有限。 “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不保證休息”,這是網(wǎng)絡(luò)工程師江一飛所在公司的口頭禪。“沒有人逼你加班,但是你不加班,明年走人的就是你。”就算周末能夠休息,單身的他往往一天用來補(bǔ)覺發(fā)呆,一天用來采購下一周所需,“經(jīng)常一整天,我沒有和同事之外的人說一句話。”
遠(yuǎn)離原有社交圈
上在職研究生的時(shí)候,出生在北京的朱先生一直不理解,班長經(jīng)常對大家說,“大家要利用這里兩年交交朋友。”深入了解之后,他才知道端倪,許多同學(xué)是在工作后才來的北京,離開了老家原有的同學(xué)、朋友圈子,在北京,社交圈非常有限。
“我在北京認(rèn)識的人,基本上是通過工作關(guān)系認(rèn)識的,大多是生意場上的利益關(guān)系。”朱先生的同學(xué)王鵬說,“如果有一天我沒錢了,有困難了,可能誰也不會來搭把手。”
王鵬曾經(jīng)跟著工作上有過幾面之緣的人一起做生意,當(dāng)時(shí)“兩個(gè)人說著掏心窩子的話”,但最終生意不順血本無歸,當(dāng)事人也拉黑不再見他。“當(dāng)初我們還是哥們,一起說著創(chuàng)業(yè)的事情,仿佛明天就能融到資飛起來。”有時(shí)候,王鵬很想把自己的苦悶和別人說說,卻發(fā)現(xiàn)自己找不到人。“在老家、在其他地方的朋友,不能理解我說的話,但在北京認(rèn)識的人,你說了,以后知道你實(shí)力不行,就沒法談生意了。”
老家在江蘇的周先生,在北京念完研究生,工作3年后,選擇了帶妻子前往上海工作。“在北京感覺沒有幾個(gè)朋友,很孤獨(dú),今年認(rèn)識的同事,明年可能就到別處發(fā)展了,沒法深交。老家的年輕人,大多就近去上海工作。” 即便在周先生在北京念書時(shí),也認(rèn)識了少量的本地同學(xué),但他發(fā)現(xiàn),這些同學(xué)都有各自的圈子,“他們會從小時(shí)候聊起,而我沒有共同的經(jīng)歷,融入不進(jìn)那個(gè)社交圈。”
網(wǎng)絡(luò)替代線下交流
江一飛之所以會一天“不和別人說話”,不只是沒有時(shí)間,也是因?yàn)闆]有必要。他每天晚飯都是吃外賣,上網(wǎng)點(diǎn)擊,坐等上門,一句話也不用說。“7點(diǎn)下班,不吃飯餓著擠地鐵很難受,到家8點(diǎn)多再做飯,快9點(diǎn)才能吃上。”
陳曉睿也是如此,她在網(wǎng)上買幾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從包包、化妝品,衣服鞋子甚至食品,久而久之,“連商場都懶得去。”到了新房裝修時(shí),裝修材料要到實(shí)體店去買,“一張嘴,感覺自己都不會砍價(jià)了,因?yàn)檫^去都是打字交流。”陳曉睿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一天之內(nèi),除了家人和同事,跟自己溝通最多的人往往是外賣和快遞小哥。
同樣的交流困境,馮悅也發(fā)現(xiàn)了。一兩年前,經(jīng)常會有同學(xué)張羅著拉群,一個(gè)群建起來,一群同學(xué)被找到,大家嘰嘰喳喳聊得挺熱鬧,但之后群就漸漸消停,聊天的僅限于固定的幾個(gè)人。“如果不見面,網(wǎng)上能聊的話題,其實(shí)就那些,你看不到真人表情,并不知道別人對這個(gè)話題的反應(yīng)。”
同樣的問題,不只出現(xiàn)在同學(xué)群里,馮悅加入了所在小區(qū)的業(yè)主微信群,大家可以交易二手商品、會員卡,甚至于出租房子,每天群里都有許多留言。但是,馮悅依然不知道對門和樓上樓下住的是誰,同樣,對門的鄰居也不認(rèn)識她。
直到有一天,暖氣出了問題,樓上的鄰居來敲馮悅的家門,開門后兩人對視了一些,想起了對方的微信頭像正好就是本人。“啊,原來你就是……”在此之前,他們聊過天,沒有見過面,當(dāng)然,聊天,用的是手指。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思政課,要以透徹的學(xué)理分析講道理
- [詳細(xì)]
- 光明日報(bào) 2023-11-14
發(fā)揮大學(xué)文化之力,培育優(yōu)秀時(shí)代新人
- [詳細(xì)]
- 光明日報(bào) 2023-11-14
特色優(yōu)化,精準(zhǔn)支持 引導(dǎo)師資良性流動(dòng)
- [詳細(xì)]
- 光明日報(bào) 2023-11-14

蘇丹留學(xué)生顏青:希望把我熱愛的漢語和中華文化帶到蘇丹
- 中新網(wǎng)蘭州11月14日電“說實(shí)話,小時(shí)候的大部分事情我都已經(jīng)不記得了,但是那幾位中國叔叔,我記得清清楚楚。”來自蘇丹的蘭州大學(xué)漢語國際...[詳細(xì)]
- 中國新聞網(wǎng)客戶端 2023-11-14
弘揚(yáng)革命文化 傳承紅色基因 加強(qiáng)長征沿線文物和文化資源的保護(hù)利用(專題深思)
- [詳細(xì)]
- 人民日報(bào) 2023-11-14

歐佩克上調(diào)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預(yù)測
- 新華社維也納11月13日電石油輸出國組織13日發(fā)布月度石油市場報(bào)告,小幅上調(diào)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預(yù)測,稱石油市場基本面依然強(qiáng)勁。歐佩克在報(bào)告...[詳細(xì)]
- 新華社客戶端 2023-11-14

教育部公布第二批1000所全國急救教育試點(diǎn)學(xué)校名單
- 中新網(wǎng)11月14日電據(jù)教育部網(wǎng)站消息,為深入貫徹落實(shí)黨的二十大精神,落實(shí)《教育部等五部門關(guān)于全面加強(qiáng)和改進(jìn)新時(shí)代學(xué)校衛(wèi)生與健康教育工作...[詳細(xì)]
- 中國新聞網(wǎng)客戶端 2023-11-14
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呼吸道疾病進(jìn)入高發(fā)季節(jié) 各地要堅(jiān)持多病同防同治
- [詳細(xì)]
- 央視網(wǎng) 2023-11-14

他們是最能抓逃犯的PTU 也是給人溫暖的警察叔叔
- 他們是最能抓逃犯的PTU也是給人溫暖的警察叔叔本報(bào)記者跟隨特警PTU巡邏,聽到了一串有意思的警察故事聽說過各地的明星演唱會上特別能抓逃犯...[詳細(xì)]
- 中國新聞網(wǎng)客戶端 2023-11-14

杭州95后小伙從出版社辭職 幫父母一起擺攤賣菜
- 杭州95后小伙從出版社辭職幫父母一起擺攤賣菜日子是自己過的現(xiàn)在的生活很安心從出版社的員工到菜市場擺攤,95后小伙林龍卻覺得,自己找到了...[詳細(xì)]
- 中國新聞網(wǎng)客戶端 2023-11-14
打假博主B太走了之后,市場上的“鬼秤”怎么辦?
- 是否使用合格計(jì)量秤、是否誠信經(jīng)營,不僅關(guān)系消費(fèi)者權(quán)益和商戶的信譽(yù)形象,也關(guān)系當(dāng)?shù)氐奈穆眯蜗蠛蜖I商環(huán)境,更是城市面貌的某種折射打假博...[詳細(xì)]
- 中國新聞網(wǎng) 2023-11-14
新華全媒+丨南水北調(diào)中線工程調(diào)水突破600億立方米
- [詳細(xì)]
- 新華社 2023-11-14
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助力貴州高質(zhì)量發(fā)展
- 央視網(wǎng)消息 貴州在實(shí)施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戰(zhàn)略上搶新機(jī),抓牢“算力”這一獨(dú)特優(yōu)勢資源,加快培育大數(shù)據(jù)產(chǎn)業(yè),持續(xù)推動(dòng)數(shù)字化與實(shí)體經(jīng)濟(jì)深度融合,以...[詳細(xì)]
- 中國新聞網(wǎng) 2023-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