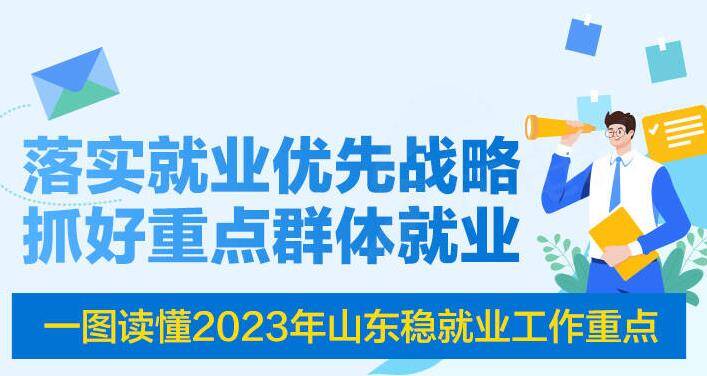文化觀察丨讓中國篆刻成為世界性的存在
來源:大眾網
2023-03-23 09:05:03
原標題:文化觀察丨讓中國篆刻成為世界性的存在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
原標題:文化觀察丨讓中國篆刻成為世界性的存在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
在一塊極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筆和結構表現種種意趣氣勢,形成各種風格流派,是中國所獨有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是活生生的、流動的、富有生命暗示和力量的美——
讓中國篆刻成為世界性的存在
3月20日,首屆中華印信文化精品展在曲阜開幕,古今篆刻珍品匯聚。“這屆印信展既有古今對話,也有國際交流,既有各創研單位的藝術骨干,也有嶄露頭角的印壇新秀,真正詮釋了傳統與創新的交融,可謂‘篆刻無限景,都聚展陳中’。”展覽主辦方之一的中國書協篆刻委員會副主任范正紅表示。
次日,與該展覽配套的“印證誠信 共鑒文明”文化學術論壇、圓桌討論會、全國印社座談會在孔子講堂舉行。在這一系列研討活動中,來自全國的數十位專家,闡述印信文化與誠信文明的歷史內涵,對“新時代的誠信精神及其價值意蘊”進行深入研討,為印信文化的普及推廣提供強有力的學術支撐,全面提升首屆中華印信文化精品展的學術高度及影響力。
“這樣高規格的展覽和論壇,在曲阜舉辦是最合適的。這里與其他地方的氣場不一樣,是圣賢之地。誠信和這里有非常濃郁的血脈關系,印信和這個地方孕育、培養出來的文化磁場是有密切關系的,這也為篆刻家體現自己的家國情懷提供了平臺”。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書協顧問、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
“印”與“信”是物證與價值觀的關系
在陳振濂看來,在尼山圍繞“印證誠信 共鑒文明”研討,要從“大印學”的角度出發,圍繞“學科交叉,文明互補”這兩大理念支點往深遠處延展,使中國篆刻成為世界性的存在。“在今天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里面,我們的印學和篆刻在‘東學西漸’時有什么樣的作為。”陳振濂說,十年以前,整個古代的印章、篆刻史的研究尚在古人劃定的范圍。“現在我們提出的概念是世界印章史,中國篆刻史很重要,是核心,但世界印章史更重要,我們提出‘大印學’概念。”
陳振濂指出,“印”與“信”的關系,是物證與價值觀的關系,是古物憑證與抽象理念的關系,是從形而下的物質到形而上的精神的關系。陳振濂首先展示了一些上古時期原始人留下的印痕,他說:“在沒有私有制的原始人時期,人類就有了‘印記’的意識,如一片樹葉、一串腳印、一個手印,都是具有一定意義的‘印痕’,人類的文明史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從‘印章’的原始痕跡‘印痕’,到今天形成‘印章’的概念,走過了整個文明史。整個文明發展史可以證明,‘信’通過‘印’來證明其存在。”
剖析開來,“印”作為物證是特別具體的,可以看、摸、把玩;“信”作為一種價值觀,是抽象理念,只存在于每個人的思想中。從形而下的物質到形而上的精神,在傳統文化中,印、信之間進行了一個勾連,這對我們研究印章是非常重要的認知前提,即沒有印不足以言信。
轉換角度,則是無信不足以證印。“印章篆刻得再好,從印章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沒有‘信’這樣一個思想支撐,這個印章不見得會有人來認可你的證明。”陳振濂說,印、信是互為循環的關系——無印未足以言信,無信不足以證信。
陳振濂用舉例子的方式,講述了印信文化的三個發展階段:第一時期,印記主要起符號標識功能,例如上古時期陶器上的陶拍,以及私有制出現后烙燙牲畜的標記。
在首屆中華印信文化精品展上,展示著數種陶拍。早在齊魯之地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時,先民使用陶拍在成型的陶器外壁拍打,清楚地留下印痕,這樣不但可使裂縫彌合,陶坯質地緊密牢固,還能留下美麗的紋飾。這種拍印紋飾的方式與印信鈐蓋的方式基本相同,許多專家認為陶拍對于印信的產生有著啟示作用。
隨著經濟發展,人們需要構建一種相互約束的渠道——以“印”來立存照,使社會更加守信。我國現存最早的印章實物發現于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
“用印來宣示所有權,保證私有財產的穩定與可靠,這時候孔夫子的‘禮’便隱隱約約出現了,人們開始有次序了。如果牽走別人的馬,這個烙馬印顯示是別人的東西,你得送還過去,這個就是次序。物是這樣,馬也是這樣,其他整個社會生活的細節里面,一定也建立著次序。”陳振濂說。
作為符號標識,印、信是合在一起的,印是宣示,信是社會共同約定俗成的規則。這個標識功能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而是用符號呢?“這和中國古代印文化的產生、當時的社會需求息息相關,跟今天在書齋里篆刻不是一回事兒。”陳振濂解釋。
“一記多制”固定、重復循“信”
印信文化發展的第二個時期,印記主要起證明功能。陳振濂解釋,這時期印記從“一記一制”發展到“一記多制”,“標記固定,則有‘信’,重復、可復制循‘信’”,還催生了印刷術,促進文明飛速發展。
春秋時期,印章主要應用于器物,一些陶斗、陶缸、陶缶上會有抑印的文字,主要功能便是憑信,證明器物的出處——作者和作坊。首先這是一種責任擔當,等于現在的質量保證,第二可以防偽,第三是表歸屬,即“物勒工名”。“從文明史的角度考慮就是證明這個是我家出產的,此時‘信’開始延伸新的文明樣式,這個文明的樣式便是‘一記多制’,后面發展到印刷和傳拓。”陳振濂說。
“這種印記的證明功能,有兩個重點可以把握,一個是固定,再就是重復,不厭其煩地重復。”陳振濂說。這一觀點,在東漢時期的學術著述中得到印證:學者劉熙在《釋名》一書中言,“印者,信也”;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也解釋,“印,執政所持信也”。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方輝,以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的視角,對中國歷代的璽印、印信進行了生動解讀。“把誠信和印章聯系在一起,是從戰國時期出現的,比如說齊國的古鉨印里面就有‘高幽信鉨’的稱呼,當時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到了戰國時期,璽印才成為一種文化和制度。”
此次印信展,有一套來自五蓮牌孤城遺址中出土的四枚戰國印,作為國家一級文物,備受觀眾青睞。“這處遺址在齊長城附近。從古印里,可以看出很多制度性的安排。這四件印非常大,幾乎是一個手把持不過來的,有的印是對山區資源的控制,有的是控制海關,說明齊長城除了軍事目的,還有經濟目的,要通過關口得留下買路錢,要交稅的。”方輝說。
方輝介紹,璽印文化還派生出一套中國獨有的保密制度——封泥。先秦時期,人們運送物件,用繩子捆扎,在繩子的打結處粘上特制的泥塊,按上璽印,用來防止別人拆開,叫“封泥”“泥封”“封緘”。后來,這一方法被用到文書的傳遞上。把竹簡放在木匣里用繩子扎好,打結處粘上泥塊,按上璽印,以作保密。
封泥不是印章,而是古人用印的遺跡。由于原印是陰文,鈐在泥上便成了陽文,其邊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寬邊。戰國直至漢魏時期多使用封泥,晉代紙張、絹帛開始盛行,取代了竹、木簡的使用,封泥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秦漢時期,出現了帶田字格的印,這個和瓦當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是鑄造的印出現了分格,可以說是現在篆刻的雛形。在秦漢時期,律令當中對印的使用有嚴格規定,官府當中要蓋印章,就是‘封泥’的制度。”方輝說。
封泥留存至今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非同尋常的學術價值。中國近代學者王國維曾說:“封泥之物,與古璽相表里,而官印之種類,較古璽印尤多,其足以考證古代官制、地理者,為用至大。”“戰國時期六國里面,齊國代表東方。齊國的官印,尤其是封泥可以說傳世出土最多。近幾年在秦都咸陽附近有很多的封泥出土。我們現在對先秦璽印研究的新材料目不暇接,一個封泥項目可以出到20多卷,是我們研究上古典章制度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方輝說。
封泥還極具藝術價值。清末以來,不少有名的篆刻家都從封泥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從而卓然成家。吳昌碩、趙古泥等篆刻風格大氣磅礴、高古雄渾、莊重虛靈,無不與封泥的氣質特點融合相連。封泥也是一部立體的印譜,可借鑒其邊欄的多變和歲月的“造化”之功,形成特殊的古味與意趣。
印信文化能成為文化交流的軟性藝術語言
陳振濂介紹,印信發展的第三時期,便是信物功能,例如皇帝印、職官印等。印成為社會階層登記、劃分之憑信。“次序越嚴整,就越需要印章的使用,因為要靠這個表明身份。”陳振濂分析。
印既是信用的憑證,到了一定歷史時期也成為權柄的象征,用固定的印記來代表個人信用或職權。秦以后,璽印常常與國運相聯系,立國的新主常常將制作天子玉璽視為第一要務。
秦漢之際,印上有鈕,綬帶穿鈕而過佩戴于身,因此印的計量單位是“鈕”。它既是信物,亦是飾物,有“佩之以綬”之規,就演變出無窮無盡的印綬美學。秦漢之印是姓名印或官職印,極其嚴肅。佩印是人格的彰顯,言而無信的人是佩不得印的。
印信的證明作用,在“信義之邦”——齊魯印信的風采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其中,除了跨越兩漢而來的關內侯金印、劉疵瑪瑙印等國家一級文物外,還有出自萊州的“右鹽主官”系鈐蓋官鹽的印信,印面有25.5cm×23.5cm之巨,若論體量堪稱古印第一;來自濟寧市博物館的“范式之印”,出土于濟寧嘉祥縣的范式墓。范式便是守信的典范人物,據說他和朋友張劭約定好兩年后去對方家中拜訪,約定時間一到,范式如約而至,張劭具雞黍相迎,二人浮一大白,“雞黍之交”的誠信故事由此廣為流傳。
隨著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等文字不斷漸進,漢以前作為書寫載體的竹木簡被魏晉紙張的發明所替代;各個時代、民族、區域的文化、審美因素和制作手段的不同,使印章有著應時、應需而產生的鮮明的時代特征。在印信展中,可以看到先秦諸侯的璽印、秦印、漢印、魏晉印及唐、宋、元印,大小、材質不一,印風魚龍變化,各臻其妙,呈現了百花齊放、移步換形的藝術內涵。
“從古人的印章到現在我們的公章、私章,各色各類的,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用得非常廣泛,應該說是如影隨形。現在更是離不開各種證書,從小到大,從校園到職場,證件必須得有章,有的還要鋼印,這是一種證明,也是信用的保障。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人對印章有著情結和寄托。”在圓桌討論會上,曲阜市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南京大學創意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周凱說,印章是誠信的基石,也是中華文化獨有的標識,可以將其列為“文房五寶”。
正如學者所言,在一塊極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筆和結構表現種種意趣氣勢,形成各種風格流派,是中國所獨有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是活生生的、流動的、富有生命暗示和力量的美。
縱觀元明清時代的印章擁有者,可以看出印章其實透露了主人的人生想法和藝術追求,尤其是印章上面的字體選擇和篆刻內容,常常表達了主人的思想情感。本次展出的一套四件蒲松齡印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以“柳泉”為典型。
蒲松齡老先生終生摯愛村東柳泉,曾說“予蓬萊不易也”。這種愛,也化到這枚小小的印章中,將繪畫和篆刻完美結合,既是一方布局精嚴、刀法靈動的篆刻作品,又是一幅有筆有墨的山水畫。印面有泉、山、垂柳、書生,運用了斜角呼應的對比關系,山崖在右上角,山泉一瀉而下,小橋上的書生面對泉水似有吟詠之狀。坡岸上柳絲飄拂,既接山泉下瀉之勢,又有向書生招手之姿。這一山,一泉,一垂柳,一書生,大小高下,比例適中,境界空曠,巧妙地體現了“柳泉居士”的意境。
印章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從實用的功能轉變為審美的功能。陳振濂從文化史的角度去觀照,大大拓展了印章內容表現的豐富度,拓寬了印信文化研究的視角。“印信文化的研究是對傳統文化‘兩創’的探索研究,印信文化也能夠成為不同國家和文化交流的軟性藝術語言。”陳振濂說。(大眾日報記者 盧昱 報道)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第二屆“鮮美煙臺好禮”征集正式啟動
- 3月22日上午,第二屆“鮮美煙臺好禮”征集啟動儀式在煙臺東山賓館舉行。本次活動由煙臺市消費者協會聯合煙臺市委宣傳部、煙臺市市場監督管...[詳細]
- 煙臺晚報 2023-03-23
男子突發心跳驟停倒地不起 毓璜頂醫院護士跪地按壓900余次奪回生命
- 煙臺毓璜頂醫院泌尿外科一病區主管護師姜月華。膠東在線3月23日訊“有了,有呼吸和心跳了。看著病人生命體征恢復的那一刻,她緊張的心終于...[詳細]
- 膠東在線 2023-03-23
山東工商學院專精特新產業學院獲批立項
- 2022年9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啟動專精特新產業學院建設,旨在遴選辦學基礎扎實、產業服務能力強的高校,聯合“專精特新”企業、關鍵產業鏈重...[詳細]
- 煙臺日報 2023-03-23
第二屆“鮮美煙臺好禮”征集啟動
- 推介煙臺好禮,講好煙臺故事。3月22日上午,第二屆“鮮美煙臺好禮”征集啟動儀式在煙臺東山賓館舉行。本次活動由煙臺市消費者協會聯合煙臺...[詳細]
- 煙臺日報 2023-03-23
全國春季游泳錦標賽:“蝶后”張雨霏亮相輕松奪冠 汪順拿下第四金完美收官
- 另一位東京奧運會冠軍汪順在男子200米自由泳中以1分47秒15的成績奪冠,收獲了他在該賽事中的第四枚金牌。至此,汪順以優異表現完結了他在本...[詳細]
- 青島新聞網 2023-03-23
中國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2屆會議堅決回擊西方國家抹黑污蔑
- 3月22日,中國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2屆會議議題四一般性辯論發言,堅決回擊西方國家抹黑污蔑,揭批西方人權劣跡和虛偽面目。中方表示...[詳細]
- 環球網 2023-03-23
獲得2022年度“山東省放心消費示范單位”
- 今年的“3·15”是第41個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為認真貫徹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切實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營造公平、誠信、和諧的消費...[詳細]
- 濟寧日報 2023-03-23
臨沂公交推出的這份攻略請收好
- 日前,臨沂公交集團推出一份游玩攻略,讓我們一起坐上公交車,好好感受下臨沂這春天的美景吧。01五洲湖臨沂市五洲湖景區,又稱為“臨沂市文...[詳細]
- 沂蒙晚報 2023-03-23
臨沂高新區成為外來投資樂土
- 3月22日上午,臨沂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高效太陽能光伏材料正式下線和臨沂高新區產業發展有關情況。中科天問生產車間2...[詳細]
- 沂蒙晚報 2023-03-23
山東膠州:金融助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 新華社青島3月22日電題 山東膠州 金融助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近年來,山東省青島市膠州市加強金融供給,全力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優先保障鄉...[詳細]
- 新華網山東頻道 2023-03-23

“抗爭線”到“發展線”:膠濟鐵路見證山東高質量發展
- 2023年,山東省委省政府做出建設文化體驗廊道、推進文旅融合高質量發展的重大部署。山東全面啟動沿黃河、沿大運河、沿齊長城、沿黃渤海、沿...[詳細]
- 海報新聞 2023-03-23
@駕駛員,青島交警發布沙塵暴天氣出行提示,請注意查收
- 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3月22日訊3月22日16時,山東省氣象臺發布沙塵暴黃色預警,目前,我省部分地區已出現沙塵天氣,預計22日夜間,部分地區...[詳細]
- 青島新聞網 2023-03-22
快訊!外媒:瑞典議會批準瑞典加入北約
- 【環球網快訊】綜合俄新社、《消息報》等多家俄媒22日最新報道,瑞典議會投票批準了瑞典加入北約。2022年5月,瑞典和芬蘭同時申請加入北約...[詳細]
- 環球網 2023-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