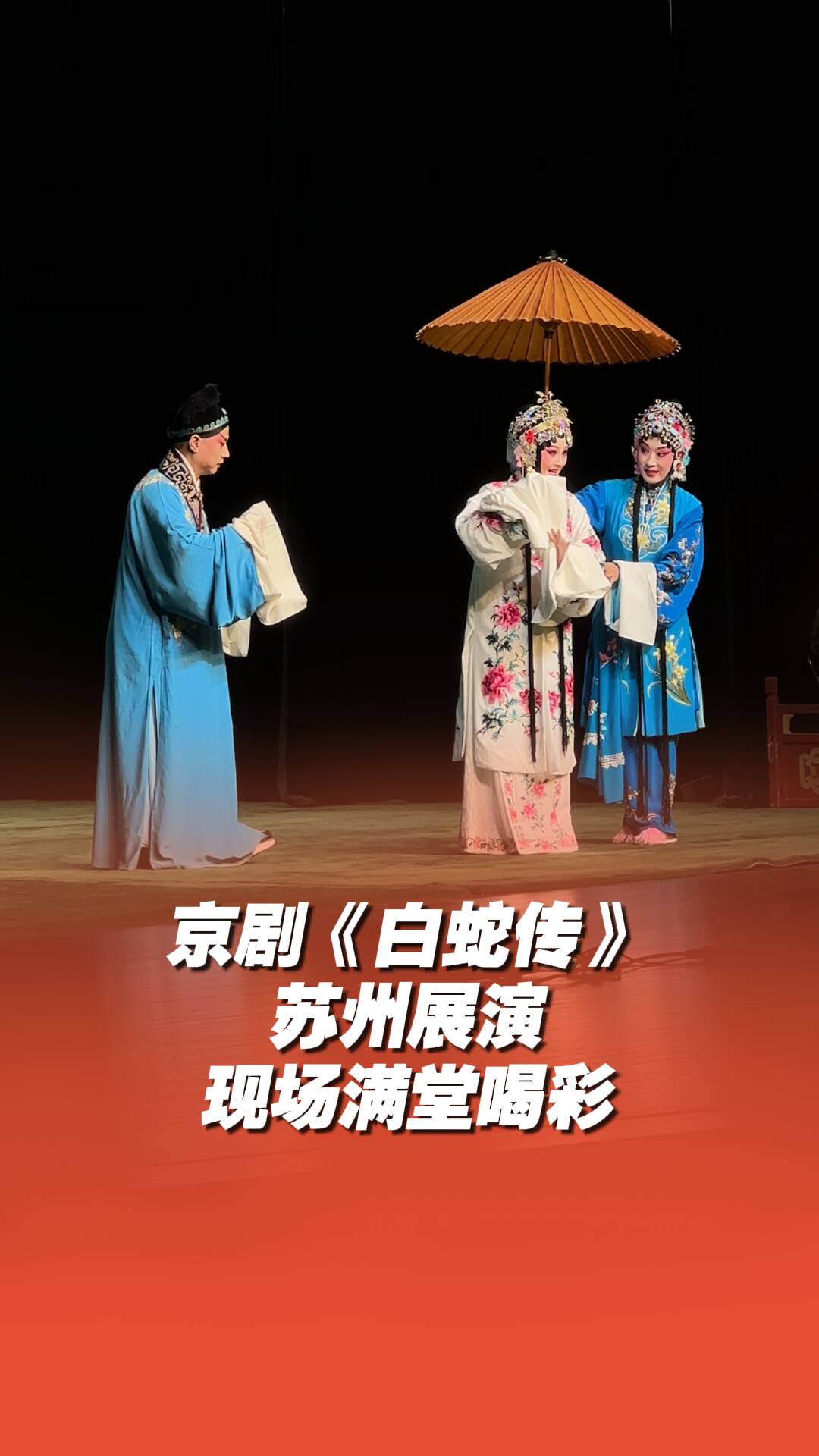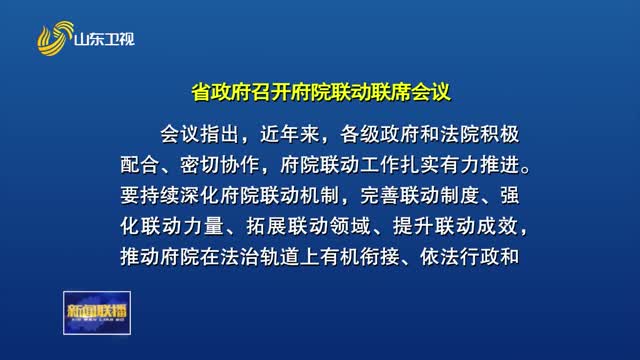山東近代的五處自開商埠
來源:齊魯晚報
2025-06-18 08:42:06
原標題:山東近代的五處自開商埠
來源:齊魯晚報
原標題:山東近代的五處自開商埠
來源:齊魯晚報
山東自古就是工商業發達的地區,西周時,姜尚被封于齊地,建立齊國之初,便“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近代以來,由于山東有港口、鐵路、運河的優勢,加上商貿基礎好,沿海和內陸開辟了很多商埠。這其中,前一階段是受外界壓力不得已為之,如1861年煙臺在英國等的要求下辟為通商口岸,1898年青島被德國強占,隨即開埠等;后一階段則是為謀求民族自強之路,主動順應時代潮流,自主建立的商埠,如設立濟南、濰縣、周村、龍口、濟寧各埠。
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1906年1月10日),山東巡撫主持儀式,宣布濟南、濰縣、周村開埠,廣招華洋客商前來投資興業。其實,兩年前,以濟南為首的三個自開商埠就開始申辦了。
□紀習尚
自開商埠
是順應時代需要
濟南商埠的建立,和當時的國內大環境以及省內小環境是分不開的。先看國內大環境,鴉片戰爭后,覬覦中國市場的列強以不平等條約的方式,逼迫中國開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稱為“約開商埠”或“約開口岸”。如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南京條約》約定的“五口通商”,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又約開牛莊、登州、臺南、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等十余個通商口岸。英、法等國不僅在此增設海關,收取關稅,奪取中國利權,還在商埠內租借土地,享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等本應屬于中國的權力。煙臺就是一個例子,開埠后設立東海關,稅務司長期由外國人擔任,中國對海關的管理權旁落。
為此,清政府深為擔憂:如果各國都來中國設立商埠,政府如何應付?當時的有識之士也感嘆:“一國數府,十國即數十府,豈非遍地通商?”既然對外通商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與其被動挨打,為什么不主動設立商埠,將利權、事權、主權都收歸名下?自主設立商埠,已成為自上而下的共識。1898年7月,光緒皇帝給各省將軍、督撫的諭旨中,首先說明國際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國均不得侵占。”接著強調,以中國的現狀,必須自開商埠:“現當海禁洞開,強鄰環伺,欲圖商務流通,隱杜覬覦,惟有廣開口岸之一法。”山東掖縣人、曾任工部尚書的呂海寰也呼吁:“中外通商以來,各國用其開通門戶之策,每次議約無不索開口岸,爭設租界。將欲杜外人之覬覦,保自有之利權,非實廣辟商場,由我自行開辟,不足以籌抵。”
光緒要求沿海、沿江、沿邊各地調查本地情況,抓緊籌建商埠:“如有形勢扼要、商賈輻輳之區可以推廣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總理衙門辦理。”不過,由于商埠對區位、交通、人口、資金、貿易基礎等硬件條件要求很高,加上當時局勢動蕩,雖然朝廷的呼聲響亮,但應者不多。只有廣西巡撫于1899年初申請將南寧辟為商埠,但籌建花了8年,到1907年才正式開埠。
膠濟鐵路
促成山東三商埠
山東的三處商埠,雖然于1904年才開始申辦,但批準、籌建較快,1906年就正式開放了。這與膠濟鐵路的營造是分不開的。
膠濟鐵路的工期進展很快。1899年9月在青島開建,1901年4月修至膠州,1902年6月到達濰縣,1903年下半年已修至周村,眼看就要抵達省府濟南。當時,山東是德國的勢力范圍,隨著鐵路向西延伸,一些德國商人提出要求,在濟南設立商行、貨棧。
山東方面感受到了這種日益臨近的危機:“膠濟鐵路不久修成,青島德商欲來開行棧者日多一日,明禁而實不能禁。與其專利德商而他商無所與,不如由我自開商埠較為有益。”為了抵制德國進一步染指膠濟鐵路沿線各重鎮,將更多的主動權留給中國,1904年春,時任山東巡撫周馥與直隸總督袁世凱共同籌劃自辦商埠。同年5月1日,兩人向朝廷共同遞交《查明山東內地情形請添開商埠折》,請求批準濟南等三地開埠。
在奏折中,周馥、袁世凱以“一拖二”的方式,申請開辟濟南商埠,并將濰縣、周村兩處作為分埠。濟南商埠的優勢,一是橫、縱兩條鐵路干線即將在濟南交會:“青島建筑碼頭,興造鐵路,現已通至濟南省城。轉瞬開辦津鎮鐵路(天津至鎮江,后延伸至南京浦口),將與膠濟之路相接。”二是原本就有黃河、小清河碼頭,水陸交會,“地勢扼要,商貨轉輸較為便利”。同時,濰縣和周村“皆為商賈薈萃之區,該兩處又為膠濟鐵路必經之道”,濟南、青島之間的貨物運輸必然要經過兩地,應該作為分關一并開辟。
正是因為形勢緊迫,奏折遞交半個月后,5月15日,清政府即批準了這個項目:“所有奏請在山東濟南城外自開口岸,并迤東之濰縣及長山縣屬之周村一并開埠作為分關一節,業經本部議復奉旨允準。”
之后,濟南商埠以及濰縣、周村兩處分埠,便緊鑼密鼓地開始籌建。
1905年2月25日,袁世凱等上奏《濟南商埠開辦章程》,共分定界、租地、設官、建造、稅捐、經費、禁令、郵電、分埠等九條。其中“定界”條,將商埠的范圍確定在濟南西關外、膠濟鐵路以南:“東起十王殿,西至北大槐樹,南沿長清大道,北以鐵路為限。”商埠東西近2.5公里,南北約1公里,占地約4000余畝。
同年農歷十二月,袁世凱等又上奏兩個章程。一是《濟南商埠租建章程》十五條,強調濟南商埠是自開商埠,具有完全主權:“作為自開商埠,與條約所載各處約開口岸情形不同,準各國洋商并華商于規定界內租地雜居,一切事權皆歸中國自理,外人不得干預。”二是《濟南商埠巡警章程》十四條。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三個章程雖然以“濟南”打頭,但濰縣、周村作為分埠,章程內容同樣適用:“濰縣、周村兩分埠均照此章程辦理,各事均歸濟埠統轄。”
以上三個章程,加上《濟南商埠買地章程》的實行,標志著濟南商埠以及濰縣、周村兩分埠基本具備了開通條件。于是,1906年1月10日,山東省舉行了隆重的開埠禮,只不過這時創始人之一、原山東巡撫周馥已經調任他職,而由新任巡撫楊士驤主持。
“官督商辦”的
龍口商埠
繼濟南之后,龍口也著手申辦商埠。龍口位于山東半島北部,開埠有三大優勢,一是交通便利,地處黃、渤海分界線附近,“扼渤海之中樞,為直魯之鎖鑰”;二是貿易發達,“每當春秋之交,商貨云集,貿易利市,誠天然之商場也”;三是與日本控制的旅順、大連隔海相望,戰略地位重要。因此,當局非常支持龍口開辟商埠。不過,由于政府財政緊張,無力注入資金,與由官方主導的膠濟鐵路三商埠不同,只能采取“官督商辦”的方式。
1914年2月2日,北洋政府下令龍口商埠開始籌辦。商埠設立了興筑公司(后改為完全商辦的“龍口商埠興筑股份有限公司”),籌集股款,負責各項建設事業。至1915年10月,界址已經劃定:北起沙崗,南至龍口舊村柵欄門外,東至北皂莊大道,西至北大圈西岬。各項工程也次第興辦,龍口正式開埠,原有的舊式碼頭也進行了升級。1918年,在北大圈偏北一帶建筑洋灰包鐵筋(即鋼筋混凝土)新式碼頭,預算大洋十二萬元,于1919年7月31日竣工。
曾為中國自開商埠大聲疾呼的山東人呂海寰,在龍口商埠的建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呂海寰的出生地掖縣,與龍口所在的黃縣相鄰,處在龍口商埠的輻射圈內,因此呂海寰對龍口商埠傾注了別樣的熱情。1917年6月6日,他被推舉為興筑公司董事會會長,作為興筑公司的重要成員,推動商埠的建設。
龍口開埠后,發展很快。據1917年7月《申報》報道:5年前,商號不過百余家,現在已有雜貨商70余家、客棧60余家、糧行50余家、行店十余家、輪船行3家、錢莊銀行40余家,此外還設立有龍口銀行。
歷經周折的
濟寧商埠
與龍口商埠一樣,濟寧商埠也是由民間主導的商辦商埠。濟寧曾是京杭大運河上的重鎮,津浦鐵路修建后,又從兗州站引出兗濟支路,抵達濟寧。龍口商埠開辟并取得初步成果后,有經商傳統的濟寧商董也希望以龍口為樣板,開辟濟寧商埠,振興地方經濟。
但是,濟寧開埠頗費了些周章。1918年起,潘復、靳云鶚等濟寧鄉紳及工商界人士按照龍口自開商埠辦法,發起籌設濟寧商埠。1919年12月,向山東省政府遞交了開辦商埠的呈文。延宕多時后,1921年6月30日,外交、內務、財政、司法、農商、交通六部以及稅務處提交了開辟濟寧商埠的呈文,一是濟寧自開商埠的必要;二是界址擬劃定在東關、南關外一帶地方,靠近津浦鐵路兗濟支線路車站;三是開辦資金,擬先由財政部墊發國庫券二十萬元,以資應付;四是征稅事宜,擬參照濟南商埠成例。
按照當時說法,濟寧商埠“系仿照龍口商埠辦理”,管理方面主要參照龍口。所以,1922年4月,山東省也相應修改了《商辦濟寧商埠章程》《租建章程》《購地章程》《建筑公司章程》等,并遞交外務部。
1922年4月22日,濟寧商埠獲得批準,正式開始籌辦。濟寧商董們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資金。濟寧商埠采取在全國發行有獎換股債券的辦法,每股五元,共四萬股,計劃募集資金二十萬元。1924年2月發行第一期,到當年7月,已發行至第七期,當期開出的中獎債券,分別由杭州、紹興、寧波、上海等地的經募商號售出。之后,債券繼續發行,但銷售情況不盡如人意,《京報》等媒體甚至認為其是“變相彩票”。
資金難以到位,地方官員督辦不力,加上天災兵禍,濟寧商埠的籌辦工作停滯不前。1928年6月出版的《戰地政務委員會公報》登載了《調查濟寧商埠》一文,認為濟寧商埠“籌辦有年,曾經耗費巨資,迄無成效可觀”,當局雖然有意繼續“遴派干員,速行籌備”,但濟寧商埠最終未如山東其他商埠一樣取得成效。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著力實現新突破!山東已累計完成老舊小區加裝電梯8018部
- 新黃河記者在通氣會上了解到,2021年以來,山東已改造老舊小區1.5萬個、270多萬戶,為確保改造有力有序推進,山東將重點做好四方面工作。著...[詳細]
- 舜網 2025-06-18
2025年度注冊城鄉規劃師職業資格考試時間定了
- 根據全國統一安排部署,2025年度注冊城鄉規劃師職業資格考試定于9月20日、21日舉行。我省有關考務工作計劃如下 一、報名安排2025年度注冊城...[詳細]
- 舜網 2025-06-18
局部或現150毫米以上大暴雨!山東將現較強降雨
- 山東省氣象臺6月17日16時發布重要天氣報告 受暖濕氣流和冷空氣共同影響,預計18日傍晚到20日白天,山東省自西向東有一次較強降雨過程,伴有...[詳細]
- 舜網 2025-06-18
因濟南鳳凰黃河大橋南延工程施工,這一地出行有變化
- 按照濟南市鳳凰黃河大橋南延工程整體施工部署,自2025年06月21日22時起對鳳凰黃河大橋南延工程鳳凰路進行橋梁主體下部結構施工施工,需占用...[詳細]
- 齊魯壹點客戶端 2025-06-17
有效借勢演唱會 推動住房促消費
- 膠東在線6月17日消息為貫徹落實上級關于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促消費相關政策,萊山區充分借勢利用張韶涵演唱會流量,于2025年6月14日組織藍...[詳細]
- 膠東在線 2025-06-17
青島機場今年日韓旅客量已超百萬人次,免簽入境者同比增長48%
- 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6月17日訊今年以來,青島機場口岸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出入境熱度。截至6月15日,青島機場往返日韓旅客量突破100萬人次,...[詳細]
- 青島新聞網 2025-06-17
更新“里子”護城市安全,山東將改造老化燃氣管網超1200公里
-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王皇6月17日,山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舉辦新聞通氣會,介紹山東推進城市更新有關情況。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城...[詳細]
- 齊魯壹點 2025-06-17
山東力推醫防融合,疾控與醫療機構實驗室檢測“資源通”
- 傳染病的有效診斷、治療與防控,離不開精準高效的檢測工作。在傳染病技術檢測方面,山東疾控機構與醫療機構是怎樣分工合作的。山東省疾控中...[詳細]
- 齊魯壹點 2025-06-17
山東407萬慢病患者納入“三高共管”,270萬完成并發癥篩查
-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賀照陽6月17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邀請省疾控局等介紹山東省深化醫防協同醫防融合,全方位保障人民群眾...[詳細]
- 齊魯壹點 2025-06-17
山東省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打造"防、治、管、康"一體化閉環
-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賀照陽6月17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邀請省疾控局等介紹山東省深化醫防協同醫防融合,全方位保障人民群眾...[詳細]
- 齊魯壹點 2025-06-17
山東省消協提醒:“第三波”狂歡618即將到來,看清套路,穩住錢包
- 中國山東網·新感知6月17日訊“第三波”狂歡618即將到來,商家們為吸引更多消費者參與購物狂歡,紛紛加大促銷力度。直播間主播們的激情喊話...[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5-06-17
2025煙臺夏季車展圓滿收官
- 6月15日,2025煙臺夏季車展于煙臺八角灣國際會展中心圓滿收官。這場為期4天的汽車盛事,吸引了80余家知名汽車品牌參展,展出車輛近千臺。同...[詳細]
- 膠東在線 2025-06-17
青島市城陽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躋身“省級臨床重點專科” 縣域醫療再攀高峰
- 2025年6月,青島市城陽人民醫院迎來學科建設重大突破——心血管內科以省內排名第一的成績成功獲評山東省臨床重點專科,成為落戶我院的又一...[詳細]
- 半島網 2025-06-17